No. 257110/09/24
文──林佑運(獨立藝文工作者)
圖──徐振輔、時報文化出版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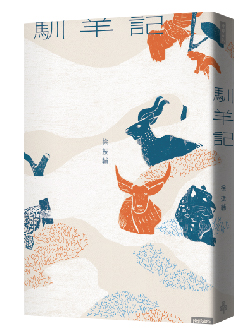
馴羊記
喜歡攝影及旅行,從昆蟲系畢業後,往地理系碩士班鑽研學問,在老師的鼓勵及支持下,徐振輔在求學的過程中,同步積累足下的旅程。將這樣的經驗與腦中所學的知識交織著關於年歲中的觀察:觀察著生態自然、觀察著圍繞周邊的環境樣貌,也觀察了棲息於其中的自己及各種生命族類。
2017年獲選「KEEP WALKING夢想資助計畫X極地科學研究計畫」成為西伯利亞極地計畫研究員,極度喜歡貓科動物的徐振輔,也前往了山水自然保護中心擔任雪豹的研究志願者。在研究的路程中,筆記本中逐漸填滿,徐振輔將西藏的旅程觀察,落筆整理篇章寫為《西藏度亡經》長篇小說寫作計畫,2019年經評選入圍「第21屆臺北文學獎──臺北文學年金獎助計畫」,2020年完成了寫作計畫後,獲選為第21屆文學年金得主,並於2021年4月底將寫作計畫更名《馴羊記》出版成書。
「此前我從來沒有意識到,原來人類已經可以創造星星了。」徐振輔在《馴羊記》的第一個篇章,這樣寫著。篇幅中描述著因為朋友「寫雪豹,卻未見過雪豹」的提問,而申請前往保育研究站進行雪豹研究工作。在藏原的夜晚,養成了望向天空的習慣,某夜發現了向著月亮滑行的亮點,經同行夥伴告知,才知道了這樣的星星是國際太空站。人類創造了天文景觀,聽來雄偉壯闊,但這背後似乎有著許多複雜的情緒可以再去探討。
《馴羊記》帶著不同的眼光,融合西藏的風土民情,以日記及抒情散記的方式,將徐振輔對於追尋雪山之王的雪豹的點點滴滴,融合不同旅者對於時代的觀察,穿梭對照,留下對於週遭的各種聲音及記述。
「回頭來看,其實我的經驗有限,沒有辦法光憑藉著閱讀資料,去虛構出一篇長篇小說。」徐振輔回憶起創作的過程,「我是經歷過自己沒有辦法寫一個純虛構的長篇小說的體悟,才完成了這樣的創作。」這個計畫有著有趣的轉折與開始,起點來自於大三去拉薩當交換生的經驗──徐振輔坐在校園中的飲料店,翻閱著手上關於西藏的書籍,資料在心中種下了點點星光,爾後在旅途的過程中向嚮導提問觀察野外生物的可能性,但生物棲息在所謂大山大河的地理環境之中,非當時觀光遊客的步伐所能踏尋。見不著面,但關於西藏的渴望,也就在心中慢慢成長,變得越來越龐大。
往後徐振輔自行規劃了很多次探索的旅程,「看動物」就成為了很重要的推力。只棲息於西藏的黑頸鶴,拜其繁殖地的研究所賜見了廬山真面目。但反倒是心心念念的雪豹,徐振輔在來來回回的過程之中,看見了身處的環境及討論的傳說、看見了足印及食骸、看見了光的殘跡及各種幻夢,就是唯獨少了這麼確實的直面相望。也因此在創作中,選擇用尋找雪豹作為後來《馴羊記》中,探討西藏文化及歷史時代的開頭,並串連起整本書的篇幅。
故事之中套著故事,尋找的旅人依附著另一個時代旅人的眼光與記憶,《馴羊記》中的徐振輔,寫自己的故事,一邊在旅途中讀著宇田川慧海的《尋羊記》並咀嚼翻譯。「每一個故事都必須放在另外一些故事裡面才能活著,好像樹要在森林裡才有生命力一樣」。翻譯的故事有轉述者,自己的故事中也有著不同的角色持續登上紙上的舞台,是過客,是主角,是每一段時光中的翩翩來去,靜待探險者解讀。
篇章之中,又有篇章。自然觀察手記之下,〈賣夢的人〉引出了〈豹子對你而言是什麼〉,描述人與獸的種種關係。問起「為什麼是雪豹?」徐振輔提及到,除了自己對於貓科動物的喜愛外,中型哺乳類也因為在體型上容易受到注目;另一方面,是因為哺乳類的保育,需要有完整的棲地及資源花費。此外,還有保育上的理由:食肉動物大多是食物鏈的高級消費者。失去了高級消費者會影響生態系的穩定。而這樣實際的人獸衝突,也是徐振輔在寫作時想探討的議題。
書寫的過程,徐振輔的日記本中,有個已落筆完成,但沒有放進書中的篇幅:冬蟲夏草。蟲草在整個藏區撐起經濟命脈,而這個藥材最高價的時候,被炒作的單位價格約莫是黃金的兩倍。如此龐大的金額,徐振輔在探索的旅途中,也有遇過當地人邀請參與挖掘體驗,實際體驗及數字計算下,理解了牧民一年就是靠蟲草季的這一、兩個月挖掘謀生。這樣的篇幅,後來留在了網路的專欄之中,深覺對議題的接觸僅止於此,但議題及其包羅的研究及討論,可以獨立成書。如果只放一篇文章在書中,可能又顯前後突兀;但如果放多了,似乎又會脫離原本的主軸,左思右想之下,徐振輔就將這樣的篇幅於書中拋去。「我們的時間都有限」,接下來的時間,徐振輔將注意力轉向不同的地點及物種,也希望每次面對一個主題,都可以用一本書為目標,去進行這樣的研究書寫:臺灣的螢火蟲、婆羅洲的熱帶雨林……等,書寫成冊對徐振輔的個人意義,「有點像是留下該留下的東西,可以不再留念。」
寫作一本書,徐振輔覺得有三個意義及目標,而這些也會彼此會互相構成這本書的樣子:為讀者寫、為自己寫、為寫作對象寫。筆下的對象,有人群、有非人物種,如何看待這樣的關聯,以及彼此參與環境變遷的過程,彷彿可以在徐振輔討論黃緣螢在都市公園的復育過程,追溯思考臺灣對於物種、綠地維持的多方面思考,看到了歷史交疊下所產生的現世面貌。從原本適合田埂間溝渠流速的螢火蟲棲地,到後續農藥使用的興起,而後轉往臺灣申請加入WTO的背景下所推動的農業轉型,與當時週休二日的生活習慣建立,徐振輔將這樣的話語,說了下來。「以前相信故事是野果,生長在一時一地,等待虔誠之人伸手摘取;此刻卻覺得語言如腳印,移動過程必然遺落隻字片語。」〈失語的旅行者〉篇章中,徐振輔悄悄地留下了這樣的註解。
Tips:臺北文學年金

臺北文學獎官網
「臺北文學年金」獎助計畫為支持、陪伴作家完成創作,每一屆均會徵選3位作家,提供獎金20萬元,由作家們於1年內完成寫作計畫後,再進行二階段決審;最後將評選出1名文學年金得主,致贈獎金40萬元與獎座。歷屆入圍並出版成書的如:徐振輔《馴羊記》、姜泰宇(敷米漿)《洗車人家》、陳柏言《溫州街上有什麼》、廖瞇《滌這個不正常的人》。更多臺北文學獎相關訊息詳見官網。